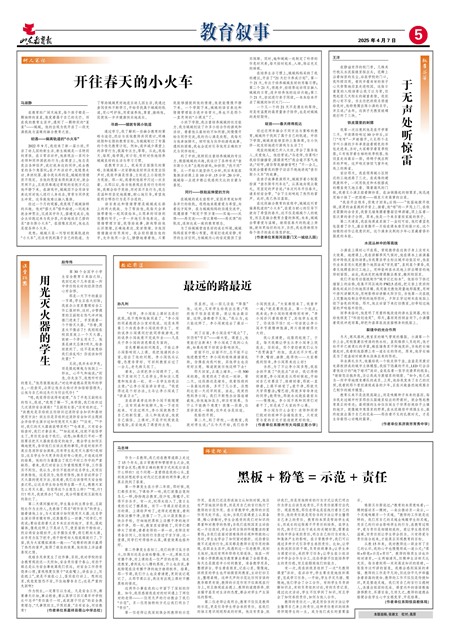于无声处听惊雷
在静谧有序的校门旁,几株夹竹桃从水泥裂缝里探出头,花瓣上沾着细密的灰尘。站在学校的门口,我环顾四周,看到步履匆匆的孩子心无旁骛地径直走进校园。这每日重复的入校场景让我习以为常,但想起前几天校长的凝重表情,我依然心有不安。当主任把班级名册递给我时,他特意圈出陈小满的名字,并且说:“去年,这孩子光教室玻璃就打坏了三块。”
铁皮屋里的刺猬
我第一次注意到他是在开学第三天。早读课铃响过10分钟后,后门“吱呀”一声被推开,只见那个名字叫小满的少年单肩挂着褪色的书包走进来。当时,大家都穿着夏季校服,只有他穿着长袖的秋季校服。他径直走向最后一排,将椅子拽出刺耳的声响。这声响足够惊飞窗外电线上的麻雀。
家访那天,我在领秀城小区附近的工地迷路了三次。在成堆的建筑废料中,一间用铁皮和木板搭成的棚屋突兀地立着。隔着漏风的门板,我看见小满正踮着脚炒菜。在油锅腾起的烟雾里,他迅速用袖口抹了一把眼睛——锅里只有蔫黄的白菜。
“我爸开出租车,很晚才回来;后妈……”他猛地掀开铁锅,滚烫的油星溅到手背上。接着,他“啪”的一声甩上门。在铁皮震颤的余音里,我瞥见墙角摞着整箱空啤酒罐,顶上压着一张泛黄的亲子合照。原来,他是一个来自重组家庭的孩子。
第二天清晨,我在他课桌里放了一盒创可贴。他盯着蓝色包装看了许久,最后竟撕开一片贴在课本扉页的裂口处。这个细微的动作让我意识到,这个满身尖刺的少年心里藏着修补裂痕的本能。
水泥丛林中的等高线
小满在上课时心不在焉,常规教学在这孩子身上没有太大效果。地理课上,我在讲解季风气候时,他在课本上画满暴雨冲垮铁皮屋的场景;当我要求学生标注城市功能区时,他在作业本里用红笔把整个地图涂成“贫民窟”。直到某个黄昏,我看见他蹲在拆迁工地上,用碎瓷砖在水泥地上拼出精密的地形剖面图。由此,我决定把地理课搬出教室,搬到校园里。
我们开始用旧报纸制作“城市记忆标本”。他拓印下拆迁墙面上的涂鸦,收集不同区域的PM2.5滤纸,把父亲上夜班的路线刻成凹凸的地图浮雕。我用激光教他测量地形高度,用树叶排列讲解风向,用树影移动讲解太阳方位。当他第一次在纸上完整地绘制出学校的地形图时,夕阳正穿过树木在他脸上投下金色的网格。那天,他主动留下来打扫教室,扫帚划过地面的声响格外轻快。
雨季来临时,他发明了用塑料瓶改造的渗水监测器,校长给他颁发了“科技创造奖”。那天,暴雨突然倾盆而下,小满攥着奖状冲进雨幕,却把外套罩在流浪猫栖身的纸箱上。
裂缝中的光合作用
冬天,寒风凛冽,教室里的暖气管突然爆裂。小满第一个扑上去,用校服裹住喷涌的热水柱。直到维修人员赶到,他才松开早已被烫红的手掌,蜷在墙角里不停地发抖,当他把长袖挽起时,我看到他胳膊上有一道长长的伤疤。原来,他穿长袖是为了遮盖幼时被沸水浇淋出来的伤疤。
毕业典礼当天,他塞给我一个铁皮饼干盒。盒盖是用废旧电路板拼成的城市立体模型。我按下隐藏的开关,LED灯会沿着他设计的“地下暗河”流动。盒底压着一张字迹潦草的纸条:“谢谢您没抛弃我,没让我成为废墟里的钢筋。”如今,他已成为一所中学地理竞赛队的成员。上周,他给我发来了自己的近照,我看到那个曾经满眼戒备的少年,正在兴致盎然地观察自己制作的城市模型。
教育从来不是浇筑混凝土,而是唤醒种子本来的基因。每当我走过城中村里那些从裂缝里钻出的野蕨时,就会想起教育真正的奇迹:最顽强的生命往往诞生于世界拒绝给予土壤的地方。就像城市角落里的野草,在水泥缝隙中顽强生长,最终绽放出属于自己的花朵——那些看不见的扎根时光,才是生命最惊心动魄的篇章。
(作者单位系济南市育秀中学)